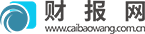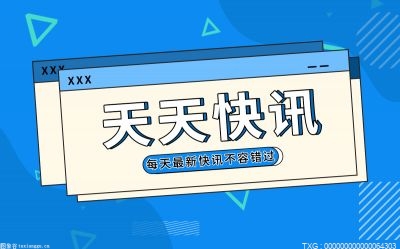作者 | 南风窗高级记者 肖瑶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下午5点整,高考数学终于结束了。
作为高考最硬核的主科之一,每年此刻,考场里涌出来的学生皆五味杂陈。有人如释重负,有人反倒更加沉重,有人嚎啕大哭,也许因为自觉失利,也许暗喜终得摆脱。
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:对于大部分考生而言,高考结束,与数学的纠缠却并未结束。
江湖有传言:“大学有棵树,上面挂了很多人,这棵树名叫高数。”除部分文科专业外均必修的高数课,历来置无数大学生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如今,一个被称作“高数救星”的人浮出水面。
在今年5月初B站出炉的“累计播放时长最高的10条视频”统计中,山东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副教授宋浩,以一己之力占据榜单第一名、第三名和第五名。
榜首的“《高等数学》同济版全程教学视频”,播放量超1亿,且断层超越第二名。紧跟其后的《线性代数》和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》,也分别被播放了超过4839万次和3283万次,日平均播放量达到最高40万次/天。
B站公布了累计播放时长最高10条视频,宋浩的高等数学课位居榜首,并独占三元
近几年来,不同学科的大学教授、学者入驻视频平台,打破知识传播的时空限制。但宋浩教的是高数,这事儿因此显得奇妙了些。
从小到大,对于数学这门高度抽象、高逻辑密度的学科,我们的恐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到了大学,在一众为高数叫苦连天的学生当中,数学之于专业学习与长远生活的意义,也再度被提出。
在宋浩的视频里,“救命恩人”“救星”“我从未谋面的恩师”等弹幕扑面而来。有人看了一学期宋浩,高数从不及格考到了八十几,甚至有线下的学生,情感饱满地写下“告白书”,讲述宋浩如何让他爱上了数学与生活。
最开始,宋浩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超级“网红”高校老师。早在2012年左右,他就开始把课堂录下来上传“优酷”或“土豆”,只是为了供学生回看和复习。那时,“网课”一词尚处于发育早期。
2014年,宋浩正式开始录课。直到五六年后,他开始在校内频繁被陌生学生认出来,线下课堂也老有外班学生来蹭。甚至有学生一面听着课堂上的宋浩,一面用手机看视频里的宋浩,前后呼应,考前突击。
讲台上的宋浩
但宋浩明确感觉到,自己成为某种教育界的“网红”,是近两三年才开始的事。2020年的一天,他在济南商场遇到外校学生激动地认出来他,还要求签名与合照。同年,B站的人也找上他。那会儿他也已经有四百多万粉丝了,如今已有近547万。
其实宋浩并不像一些擅长口才的学者那样,能把课堂变成百科全书和脱口秀,他自己也明白,“没有人会在上厕所、等公交的时候看几集线代”。他会偶尔讲几句段子和笑话,但大多都有点冷。有时他会手脚并用阐述一个公式,会用概率论谈谈自己的感情史和恋爱观。
作为一个“网红”教授,他似乎显得太“普通”了,但作为一个大学教授,他显得又太“活泼”了。
这位“亿级up主”教的高数与其他高校老师究竟有什么不同?从中小学到大学,为什么数学总让人闻风丧胆?为什么有些可以在中学考高分的人,到了大学却学不懂数学?
在教学与考试之外,我们又能如何理解数学在当下时代的地位和意义?它的美感还可为生活带来哪些指引和回音?
宋浩
成为“红人”后,宋浩的生活被塞进了些前所未有的事项。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,他先在周五下午参加了一个交流会,晚上参加了B站组织的毕业生报告会,周六又奔赴辽宁与大一大二学生见面。
在这趟繁忙的周末间隙,我与宋浩通上了话。星期天一大早,刚过八点,他就准备好采访了。我睡意惺忪,他则和课堂上一样中气十足。我们聊起高数这头“猛兽”,也谈了谈这个时代的数学与数学教育。
从零开始的数学课
作为一个没有上过高数的文科生,在打开宋浩视频后的三十分钟后,我竟恍惚地产生了回到高中课堂的错觉——
在中学阶段,你也许遇到过那样的老师:以“让你搞懂”为终极目的,用最朴素的口语,最原始的板书,一笔一划带你推导。怕你听不懂,也怕你考不会,像个操心的老父母。
在宋浩眼里,学习“高等数学”的关键,不在于“高等”,而在“基础”二字。
“对比中学数学,高数很抽象,一上来就是很多公式和符号,很多学生一看就被吓跑了。把大家领入门,先把基础的题目做出来,这个挺重要。”
学生们纷纷在宋浩b站的教学视频开头发送弹幕:梦开始的地方
在宋浩的线上学生里,诸如“终于听明白了”“听了一上午课不如来听两分钟宋浩老师”“一句话讲明白了我好几节课都没听懂的内容”等等评价层出不穷,评价大多来自大一二的初阶高数学生,包括不少“专升本”打卡。
宋浩简直要从头开始讲数学是怎么一回事。以简讲繁,把公式拆开,用自己的方法还原一个理论的推导过程。
讲极限定义,他将符号“∀”解释为“任意Any”,只不过把A倒着写;
将“存在”的英文单词“Exist”颠倒过来写,就有了“∃”存在;
讲二阶行列式,他把组成对角线符号的表达式“|a,b;c,d|=ad-bc”化写成“爱你一(-)辈子”;
讲圆柱体积“V=S*h”,“S”是底面积,“h”是高,然后嬉笑道:“Sh,宋浩嘛”。
“Sh,宋浩嘛”
一些俏皮话其实算不上多么新颖和讨巧,甚至有些上了年纪的土味感,像中学课堂上的老师,以让学生记住为唯一目的,但正是这种目的的单纯,显得宋浩的俏皮话尤为可爱。
比如宋浩自己发明的各种以形释义,“把M给摔倒”后是连加,把“π”两个腿儿捋直后是连乘;函数中自变量X对应唯一一个因变量Y,“这叫‘一夫一妻制’,一个X不能对应多个Y,因为‘一夫多妻’是违法的。”
姚杉是山东财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大一的学生,这学期上宋浩的《线性代数》,上学期她在另一位老师那里上,用PPT,好处是“清晰、直白”,但听了好几节下来,还是茫茫然。在姚杉看来,PPT就像把所有重点都堆上去,搭建成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山,但宋浩老师的板书,会告诉你这数学的高山是如何搭成的。
“数学非常适合写板书,适合一笔一划写出来,每写一个字,就是一个过程。”在宋浩看来,黑板和粉笔搭建了一个解释平台,而数学理解里,过程是不可或缺的,有了“从左到右”的推导过程,思维就有了显影,学生也跟得上。
“说白了就是用正常人、普通人的思维方式。”宋浩认为,一个好老师应该有本事把困难的东西用简单的方法讲出来,“但凡老师遇到一个地方需要动一下脑子,对学生来说可能就是很困难的东西。”
把自己放在与学生同频的位置去讲高数,做课堂的引导者而非主导者,宋浩的这种教学理念,并不是他从一开始就参透的方式。
宋浩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一个小山村,在小镇上完成了小学到高中的学习生涯。在山东大学读完了本科与硕士后,2007年,宋浩考入中国科学院读博,师从华罗庚的学生,用他的话来说,算是华罗庚的“徒孙”。
高考那年的宋浩
实际上,对大多数纯理科专业而言,当一个人钻研到了一定深度和高度,反而有可能忘记了基础起步时自己遇到的困难。这种专业密度上的“居高临下”,可能出现在经历了硕博等漫长学途的高校老师身上。
“很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很痛苦,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很简单吗?还需要我讲吗?你看一眼不就明白了吗?”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,宋浩也是这样。他把刚拿到手的大一教科书翻开一看,懵了,“这玩意儿还用学?这不跟吃饭睡觉一样简单吗?”
后来他静下来琢磨,发现现在的大学教材其实是很简略的,“比方说讲线性代数,课本里可能一个图都没有,完全是抽象的,向量之间的关系、线性空间到底是什么东西?完全不好解释。”
宋浩觉得,“上课的流程应该跟教材是不一样的,教材可能先写定理再写流程,上课是不是可以颠倒一下?先举一两个基础的、小的结论,再推导到定理。”
如今,系里新入职的数学老师在上第一节课之前,几乎都会把宋浩的视频翻出来看一遍。在这个意义上,老师或许和学生一样,也得经历一个“走进大学教室”的过程。
“好的课堂,没有围墙”
如今,宋浩每天去上课都要背近二十斤重的背包,除了课本,里面还包括一台4K索尼摄像机,一个麦克风,一只折叠小型脚架。每节课开始前,他至少得提前十五分钟到教室,调适参数,把脚架架在最后一排桌子上,镜头越过学生,对准讲台。
过去九年来,几乎天天如此。
拍摄、剪辑、压缩、转码和上传,全都由宋浩一个人完成,“采编播一体化”。自从2014年开始录课到现在,前前后后一共换了7个DV,家里光是用来剪视频的电脑就有4台,24小时连轴转。
就像他在采访里反复强调的那样,其实一切行动与求知都得发自内心最原始的热情。还在读书的时候,宋浩就酷爱琢磨摄影,硕士毕业时,全班的纪念光盘就是他一个人拍摄、剪辑和制作的。
宋浩课前调试摄像机 / 山东教育卫视 · 教育筑梦人
2014年下半学期,宋浩教过的几个学生向他诉苦,说新学期的《线性代数》听不懂,问能不能去听他的课。
但宋浩那学期在另一个校区上课,跑来跑去很麻烦。正好那部分课程他也在教,他遂萌生了录下来发给学生单独听的想法。
最初用的是录音笔,但没有画面,效果不好,便花800块买了第一台二手DV。
一开始只有几十个熟悉的学生私下传阅,一两个月后,宋浩偶然发现,下载量已不知不觉已经有了几千。再往后突飞猛进,从几万到十几万呈指数型增长。
接着,他开始上传视频课件到“优酷”“土豆”网,那会儿还没有4K,画质感人。但一名宋浩的“初代学生”回忆,从那时候开始,宿舍、图书馆,就已经到处都是抱着电脑看宋浩的同学了。
宋浩早期在b站的视频
早些年,宋浩喜欢在课堂上放飞自我讲感情史,现在回想起来他自己也有点窘,一时嘴快覆水难收,“哪能想到后来这么多人(看)?”于是,全国数不清的学生都知道了:山财的宋浩,曾在雪地里等了一个女孩足足七个小时。
那是在二十年前,宋浩还在念大学。时逢“2002年的第一场雪”风靡全国,一个大雪纷飞的济南冬夜,他跑到喜欢的女孩家小区门口找她,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三年的恋爱长跑。宋浩沿用至今的网名“ice_mouse”,也和那段年少的记忆有关。
“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嘛。”二十年后的宋浩对着学生和镜头,有些腼腆,“现在嘛,值得我在雪地里等七个小时的女孩可能只有一个,那就是我女儿嘛。”
几乎所有学生也都知道宋老师是个女儿奴。不论讲什么,都可能将他的思维牵引到自己还在学龄前的小女儿身上,课堂上,他手脚并用模仿机器人讲球坐标,又忍不住喜上眉梢:“我女儿最喜欢”。
“一节课九十分钟,要求学生全神贯注是不现实的。”于是他偶尔唠唠自己的私生活,也尝试过跟上年轻人的潮流,比如娱乐圈的“现男友”“迪丽热巴”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教学与传播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池里的东西,“改变命运的屏幕”也是2018年才第一次出现,掀起了人们对知识共享的关注。而到了今天,仅在高数界,除了宋浩之外,还比如百万级粉丝的考研名师李永乐、汤家凤,高中数学的赵礼显,等等。
其实宋浩从一开始就对教育野心勃勃。当年刚站上大学讲台上,他就在想,“北大的数学系好,清华的数学系好,山大的数学系好,但北大清华有哪个数学老师,讲课讲得全国都知道?”
开始录课以后,想法遂更大胆起来:迟早有一天,要让全国学数学的学生都来看我的视频。“我们山财可能学校不咋地,但并不妨碍我们老师把这个课讲好,我要让全国的学生都知道,讲数学的有个宋老师。”
“好的大学没有围墙,好的课程也应该是。”他想,一个大学老师不是只能困在教室里,下课拍拍屁股就走,可以利用网络把课堂延展。
九年后的今天,山财2022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叶华去学校图书馆自习,发现“四个复习高数的,有三个都在看宋浩”。这并不夸张,因为在各处平台都能听见类似描述,俨然一道校园风景线。
大一下学期,叶华第一次在课堂上见到了传闻中的宋浩。他看上去比视频里要高,一米八好几,头发多些,也爱笑。第一节课,宋浩就半开玩笑地跟同学们讲:“你们不听我讲也没关系,反正下去不懂,都会再翻我的视频出来看。”
宋浩被学生称为“高数锦鲤”
对于自己的受欢迎度,宋浩蛮自信。近两年来,他会以一种积极和热情的心态去拥抱“流量”。他在微博里为自己打广告,牢记每个平台的粉丝数量和播放量,他希望让自己的课程传播得越远越好,越广越好。
“在流量的世界里,俺们数学也有一席之地,这不挺好吗?现在一些年轻人拜明星、网红,为什么不能也崇拜一个传播知识的人呢?”
数学的城堡与高山
“高等数学”从定义上与中小学的“初等数学”划分开来,但某种角度而言,学习数学,不论是方法还是原因,中学和大学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不同。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第十八届文津奖推荐图书《心中有数:生活中的数学思维》的作者刘雪峰同样认为,在高等教育里,数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最大的特点是“严谨”。而越是严谨,越应该重视基础。
“所谓基础,就是一个一个的数学概念,它们不断推演,就把整个知识体系搭建起来了。就像一颗颗葡萄,你得把它们一串拎起来,不能散着东一把西一把。”
刘雪峰认为,“高数知识点是一层一层垒上去的,中间只要卡住某个点,可能整个链条就断掉了,后面就听不懂了。”因此,过程也特别重要。
今天的大学数学教材都挺薄,对比起来,国外的教材动辄好几千页,“因为它把每一个概念的道理、历史都给你讲出来了,当你清楚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的时候,你就知道了怎么去运用它们。”
高数教材的多个版本
怎么确定自己能掌握这个概念呢?“你把它单独拎出来,试试看能不能用生活中的语言去解释它,能不能与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。”这种生活化的理解方式,也与宋浩不谋而合。
时至如今,数学学习的必要性仍然面对质疑,尤其是当学生们在“高数(树)”上高高挂起的时候。在刘雪峰看来,数学价值的显影必然不会是立竿见影的,通过学习培养“数学思维”,才是长足的精神投资。
大量专业人员比如设计师、工程师,都“需要能把现实难题提炼成一个抽象问题”的数学思维能力,还有一些前沿科技,比如刘雪峰参与过的神舟飞船发射,“在飞船导航、控制等许多任务中,都需要用到数学”。”
而对剩下大部分普通学生来说,“数学也有益于培养一套对生活有用的思维方式,比如概率论,就可以帮你用确定的理性去辨别现在网络上很多谣言。”
理想的数学教育,也讲求与思维的动态结合。丘成桐曾在自传里提到自己对数学教育的看法:“大部分从事数学教育的人只研究如何教数学,而不讲求数学的内容、目标和意义。”
刘雪峰认为,在大学里,一个数学家未必是一个完美的数学老师。“如何以一种所有学生都能接受的方式讲数学,用大白话把一个困难的概念讲清楚,这甚至不只是一种技术,而是一种艺术了。又或许是需要一些天赋的。”
热爱数学与教育的宋浩,显然属于此列。
对宋浩的“亲学生”齐思贤来说,高数最难的地方在于其高度抽象性,“而且大学刷题时间少,很多知识点掌握不熟练,很手生的感觉。”
比如极限定义,在课上听了一遍后,齐思贤完全搞不懂,后来听宋浩用一句话解释:“当自变量趋近于某个特定值时,函数的值会趋近于一个确定的常数。”齐思贤忽然觉得脑袋里一声钟响,“原来这个概念本质如此简单又深刻”。
宋浩的长处,并不在把数学变成“花”,反而是有耐心与热情去剖开数学的土壤。而这一点,在部分学生体会到的高校课堂里则是缺席的。
从辽宁沈阳南下到南京上大学的金融系大一学生李晌,第一学期的线性代数勉强过线及格,他甚至感觉,“如果我的高中数学老师来给我讲高数,可能都不会考这么低”。
“高中老师会完全把推理过程写给你看,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先到这一步才能到下一步,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变形。(我的)大学老师就是把课本上的东西搬到PPT上,只保留关键过程,为什么这么做也不告诉你。”
李晌只好强制自己去适应这种方法,结果就是:“学会了死记硬背,背下那些步骤、公式,但要是让我运用、实践,可能真的不太行。”
课程结束后,学生刷屏感谢宋浩老师。宋浩往往可以将复杂的知识用学生能理解的大白话讲清楚,这是他的课受到那么多学生喜爱的原因
在我国目前的高校教育里,一些具体的客观环境掣肘的确让课堂与学生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。如刘雪峰提到的,“像高数这样公共课的老师主要以教学为主,并不从事太多科研工作;而教学和科研两肩挑的老师,科研的压力会挤占大量用于教学时间。因为对他们来说,申请项目、指导学生、发表论文对于在晋升和考核上的重要性,可能比教学要大得多。”
南风窗曾在2021年采访过几名青年教师,其中,一名西安某985高校信息管理系教师表示,备课与上课其实仅占工作生活的极小部分,大部分时间都被行政任务、课程活动等琐事填满;另一名三十岁的教师则表示,在“非升即走”的竞争机制下,老师最终能否通过考核,“关键不再是授课能力,而是科研成果与论文发表数量”。
在今天的大学里,高数究竟更多被当做一个工具还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培养,是教育者与学生共同的选择,还是各自实现目的的工具?刘雪峰还指出,“很多大一大二的学生学习的动力不在兴趣,而是在GPA、保研会不会加分、能不能出国等等方面。”
不过,宋浩,以及越来越多的“宋浩”们,让我们看到了好的一面:“优秀的高数老师越来越多了,有越来越多数学学者肯花心思去研究怎么教数学,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主动去寻找资料,数学的世界,会越来越开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