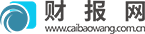白蛇被她视为一次重生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谭元元的日程很满。排练间隙的午休只有1小时,她套了件松松垮垮的卫衣,脸上还带着戏装,匆匆忙忙就来了。
但往那儿一坐,你立刻就知道,这是个跳舞的人,而且是跳芭蕾的。
细长的脖颈,小巧的头颅,永远高昂着的下巴,即使疲倦也绷得直直的背,天鹅一样优雅又孤傲,让在场每一个姿态懒散的人都不好意思起来。
但女神没有一直只当天鹅。这一次,她选择挑战一个更东方的角色——白蛇。
人生的前半程,她获得了华裔舞者能在国际上摘取的极高荣誉,是欧美国家顶级芭蕾舞团里唯一的华人首席,2004年登上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封面,被评为“亚洲英雄”。
旧金山甚至还有个专门的“谭元元日”,纪念她被授予市长艺术奖。
而现在,45岁的她又回到了自己的文化土壤,在家乡上海,演一个传统的中国故事。
周末的世界首映座无虚席。很多人都说,想象不出比她更完美的白素贞了,清纯和妩媚的混合体,还带一丝仙气,看似柔弱的身体里,却有敢爱敢恨的生命力,展示了东方女性独有的美。
她也是真爱这个角色,每次提起,眼睛都发光。
“这部《白蛇》,对我来说是一次‘重生’,让我再次意识到了‘我是谁’。”
01
舞蹈的世界是寡淡的
但值得付出代价
为了这场演出,9月中旬,谭元元从旧金山飞回上海,秋老虎的高温一下子让她有些不适应。
她常说,上海这些年的变化很大。但她真正去感受这些变化的机会其实很少。
©️上海大剧院
她每天的训练时长都在7小时左右,像最近这种有演出的情况,还要更辛苦一些。这两天,剧组在上海大剧院进行最后的彩排,早上9点从酒店出发,经常练到半夜才能结束。
难得有休息的时间,她基本都用来做理疗了。正骨、针灸、按摩……她都熟门熟路。至于女孩子们普遍喜欢的探店、逛街,“我觉得太累了,我宁愿多睡一些觉,拉拉筋什么的,对我来说就是放松了。”
©️上海大剧院
以前有人问过她,这样的生活有乐趣吗?身为舞蹈演员,饮食一定是要严格控制的。“吃一个三明治下去,很可能服装就穿不进去了。”
去旅游也是件麻烦事,每到一个地方,她都得先找练功房,否则就住不下去。“就像那句老生常谈:一天不练,自己知道。两天不练,老师知道。三天不练,观众知道。”
舞蹈的世界是单纯的,也是寡淡的。但谭元元不介意,跳舞这么美好的事,值得为此付出一点世俗生活的代价。
©️上海大剧院
这次排《白蛇》,她不仅是主舞,也是第一次担任全幕舞剧的艺术总监,因此压力更大。
《白蛇》是她从小就喜欢的故事,有各种戏剧、舞蹈、影视的版本,而这一版尤为特别,让她眼前一亮。
白蛇和青蛇其实是一体两面,白素贞贤淑的外表下,内心其实也有着小青那种向往自由快乐、追求独立自主的意识。
那种原始的、野性的力量,吸引着白蛇的觉醒,找到更真实丰满的自我。
©️上海大剧院
对谭元元来说,跳舞这些年,也像蛇蜕皮一样。“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和蜕变的过程。”
“我希望能把它打造成一个世界性的舞剧,不仅可以在大剧院演出,也不仅是在全国巡演,最终我们还是要让中国的故事流传到世界上去的。”
©️上海大剧院
这个想法听着飘渺,其实是谭元元这些年来一直坚持在做的一件事。她策划的项目《谭元元和她的朋友们》,多次通过自己的人脉,把世界一流的芭蕾明星带到上海演出。
连向来毒舌的金星,在介绍她时,都不吝赞美之词,称她是“华人的骄傲”。
而华人的身份,在芭蕾的世界并不是一张通行证,反而意味着她要付出比旁人更多的努力。
02
抛硬币决定的命运
第一位亚裔首席
谭元元是1977年生人。她学芭蕾的时间不算早,11岁,正好卡在还来得及培养“童子功”的最后时机。
那一年,她在学校操场上玩着单杠,突然吸引了一个老师的目光,走过来让她把鞋脱掉站直,又摸了摸她的肩膀,叮嘱她回家告诉父母,准备参加上海舞蹈学院的面试。
老师觉得,她天生是跳芭蕾的料,头小腿长,比例极优越。
©️上海大剧院
舞蹈学院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苗子,很快发来了录取通知书,但谭元元的父母却犹豫了。
做工程师的爸爸很反对女儿走这条路,觉得这是西方的艺术,中国人搞不出名堂,还要天天穿那么短的裙子,实在不合适。妈妈则是极力支持,两人争执了大半年也没结果。
最后,他们干脆拿来一个5分钱硬币,向上一抛,妈妈赢了。命运给谭元元做出了决定。
从舞蹈学校毕业后,谭元元拿到奖学金,前往德国留学,很快因为在国际比赛上崭露头角,被旧金山芭蕾舞团看中,成为独舞演员。
一张亚裔面孔,想在以白人为主的芭蕾舞界站稳脚跟谈何容易。对舞团的一些成员来说,这个中国女孩是个“入侵者”。
她刚到美国还不会说英文,跟舞伴只能打手势沟通,闹过不少笑话。
每到周末,她就坐两小时车,到唐人街打越洋长途回家,“因为那里便宜,一分钟3美元。”电话接通后,听到妈妈的声音,谭元元不说话,“就是猛哭。”
哭完了,电话一挂,她再乘车回来,给自己疯狂加练。
好在机遇没有让她等太久。有一次团里排《斯特拉文斯基小提琴协奏曲》,曲子难度很大,接连两位首席舞者都受了伤,无法登台。团长临时决定让谭元元试试,但只给她一个晚上的时间学会所有动作。
“我当时甚至没听懂他在说什么,只是大致猜着他的意思,然后一直点头。答应下来后,一看录像带,才傻眼了。”
大家都没抱什么希望,连替补的表演都安排好了。没想到谭元元连夜苦练,居然真的做到了。
经此一役,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,很快晋升为首席。一般人需要花12-16年时间做到的事,她只用了1年半。
一些不好听的声音也随之而来。“当时我是最年轻的首席舞者,也是第一位亚裔首席,所以容易被人戴着有色眼镜来看。”
她平时爱穿软一些的舞鞋,通常都是自己缝好后,上几次课、再排练几次,鞋子就软了,也合脚了。但有一回上台演出前,她的鞋不见了,她只能临时再缝一双,凑合穿,演出时跳得很不舒服。
从那以后,她永远是缝两双鞋备着,而且必须随身携带,连坐飞机都不会托运。
“一开始的确很沮丧,我就想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。”但现在再提起这段经历,谭元元早就云淡风轻。“你也控制不了别人怎么想你,就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、把每一个角色演好就行了。”
说完对我温柔地笑笑:“不然怎么样呢?难道跟他们吵吗?”
03
“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
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爱它”
旧金山芭蕾舞团的合约是一年一签,为了不从这个位置上掉下来,谭元元身上绷紧的弦就没松过。
19岁那年,谭元元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全幕舞剧《天鹅湖》。在普通人的观念中,跳白天鹅是芭蕾舞者的最高理想,但谭元元却没那么喜欢这个角色。
她喜欢的形象,都是内心戏丰富,甚至有些痛苦和痴狂的。第一次找到这种感觉,是在她23岁跳《吉赛尔》的时候。
为此,她也受了舞蹈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伤。在做一个大幅度跳跃时,她想跳出那种燃烧生命的、极致的热烈,因此在空中尽力把自己的腰压得更弯,腿抬得更高,突然胯骨就传来一阵刺痛。
忍到第二天醒来,她已经连坐都坐不下去。找医生一看,才知道是胯骨脱臼了,“右腿比左腿长了好多。”
随之而来的还有撕裂。医生本来建议她做微创手术,但很可能导致不能再跳芭蕾,她当然不愿意,生扛了过来,至今每到下雨天胯骨仍会隐隐作痛。
“芭蕾舞演员的忍痛力是普通人的10倍。有一次肾结石,我忍到第3天,才不情不愿去了医院,把医生都吓坏了,因为一般人一个小时就受不了了。”
但舞蹈演员的花期何其短暂,到了35岁,谭元元开始有了“退休”的念头。
“一般舞者到了30岁以上,可能在技巧上和体力上都到达了一个高峰。但如果之后没有好的作品,你就觉得好像高度再也上不去了,到瓶颈了。”
这时候,《小美人鱼》适时地出现了。
这个为爱放弃鱼尾、最终化为大海上的泡沫的故事,让谭元元每次演的时候,自己的心也在碎。
“我觉得小美人就是我,因为我爱上的这门艺术,就像小美人鱼爱上王子一样,虽然有这么多痛苦,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一样,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爱它。”
此后,她在台上一跳又是10年。身边的同龄人早已挂靴,连搭档了19年的舞伴都因浑身伤痛退休了,只有她跳到了现在。
我问她有没有想过,万一有一天不能跳舞了怎么办。她回答得不假思索:“不是万一,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。”
“芭蕾对美非常敏感、也非常苛刻,注定了我们的艺术寿命是短暂的。但那又怎么样呢?我只要能尽力延长它就好了。”
如今,当45岁的她在台上踮起足尖,演绎仙气十足的白蛇,似乎又一次重生,找到了新的自己。
©️上海大剧院
文、编辑/strawberry
图片来自受访者